更大的研究团队是否意味着导师制度和伦理道德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在一月份的国际结晶学年(IYCr)开幕式上,美国费城福克斯大通癌症中心的Jenny Glusker发表了关于结晶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讲。她的演讲描述了该领域的传统——格鲁斯克本人就是这些传统的化身。格鲁斯克在多萝西·霍奇金的实验室里工作,霍奇金是德斯蒙德·伯纳尔的博士生,伯纳尔是威廉·布拉格的protégé,在1912年马克斯·冯·劳埃开创性地发现x射线衍射之后,威廉·布拉格开创了这一切。

这种科学谱系是相关人士的骄傲,但它不止于此。一个科学家从她的导师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技术训练,还有一种文化——一种对所提问题的重要性、回答问题的方法以及研究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的认识。例如,很难想象有人会从伯纳尔的羽翼下走出,不受严格的学科界限限制。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一种道德和伦理责任感。
成长的烦恼
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卢卡IMT高等研究所的亚历山大·彼得森和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同事在一份预印本中提出,大型研究团队的趋势可能会产生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一趋势已被广泛讨论,其中一个暗示是奖励科学成就的旧机制——个人奖,尤其是诺贝尔奖——正在过时。彼得森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些指标证实,在各个科学领域,论文合著者的数量正在上升,而且单一的诺贝尔奖现在相当罕见。
这对功劳的归属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这种功劳对年轻研究人员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更不用说简单地组织大型团队以使他们高效工作的难度了。但这一趋势也对整个科学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团队越大,透明度就越低。很难监控谁在做什么,而且越来越有必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做出每一项贡献。彼得森和同事们认为,这可能会使不当行为更容易被忽视,而且不太可能会有导师的渠道来劝阻它。无论公平与否,一些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因明显未能充分审查下级同事伪造的结果而名誉受损:20世纪80年代末,生物学家大卫·巴尔的摩(theresa imanashi - kari案例),21世纪初,物理学家贝特拉姆·巴特洛格(Bertram Batlogg)在纳米技术诈骗犯Jan-Hendrik案例中(Schön)。两位高级官员都是大实验室里的大忙人。自那以后,这种情况无疑变得更加难以管理。糟糕的管理程序显然让年轻的法医化学家安妮·杜可汗伪造了马萨诸塞州欣顿实验室的数千份药物检测结果,导致Dookhan的刑期去年年底。
这该怪谁呢?
这些案例可能是极端的,但彼得森和同事们认为,在大型团队中很难维持责任链和良好的行为。当事情出现问题时,可能几乎不可能追究责任。大型团队也增加了潜在的利益冲突——比如研究人员对合作者的手稿进行同行评审——同时使他们更难被发现。彼得森及其同事写道:“在这方面,我们一直在目睹科学家和科学大众之间冲突的出现。”
其中一些担忧与价值观有关。彼得森和他的同事们继续说:“许多年轻科学家很可能被大项目的博士后陷阱‘引诱’了。”“下一批科学家是被训练成领导者,还是只是适应大型生产线?”一旦他们进入终身教职轨道,他们观察到的教训是否反映出积极的科学价值?还是它们反映了一个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生产力体系,以及与社会有益进步背道而驰的病态竞争态度?”
这种态度可能是主流文化强加给年轻研究人员的。在IYCr的开幕式上,一群年轻的晶体学家讨论了他们和他们的同行面临的挑战,并发表了一份签名声明。报告称:“年轻的研究人员面临着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对取得成果和在顶级期刊上快速发表论文的期望高、工作不安全感以及大量教学任务等问题。”这些压力正在加剧,它们阻碍了探索原创和创新方向或思考长期研究目标的自由。”They can also motivate misconduct: Dookhan admitted, for example, that she faked results because of ‘her desire to be seen as particularly hard working and productive’.
庞大的团队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它们对导师和道德的影响需要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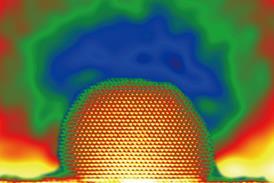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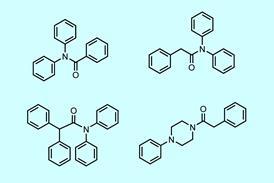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