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文化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是研究人员的重中之重

3月6日至8日在英国伦敦克里克研究所举行的第三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不是常规的科学会议。首先,这是在贺建奎重新出现的阴影下发生的,他在2018年宣布,他已经在人类胚胎上使用基因组编辑进行体外受精,导致双胞胎女婴的诞生。他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了一种名为CCR5的基因,希望赋予婴儿对艾滋病毒的抵抗力。这项工作没有得到适当的授权,他被中国当局以渎职罪判入狱三年。但他现在已经开始了再循环今年2月,他在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 at Canterbury)发表了讲话。他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后悔,这些行为受到了从事基因组编辑工作的科学家的普遍谴责。他一度有可能参加克里克的活动,但他没有。
更重要的是,与会者必须走过举着“停止设计婴儿”和“再也不要优生学”等标语的抗议者。压力团体“停止设计婴儿”称这次峰会是一场“不加批判的技术炒作盛宴”,通过倡导人类基因改造(HGM)合法化,复活了“优生学的幽灵”。他们说:“普通人必须团结起来,抵制这些技术官僚想要强加给我们的设计婴儿优生学。”“HGM并不存在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那么这次峰会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但在会议内部,故事看起来与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恐惧截然不同。分配的空间用于讨论伦理和文化因素,从“生物黑客”和“社区科学家”的角色到患者倡导团体,以及文化信仰(如毛利社区的文化信仰)在告知对基因组编辑的态度方面的重要性。这次会议绝不是狭隘的基因组推波助澜。委员会还听取了美国妇女维多利亚·格雷(Victoria Gray)感人的证词,她通过对血细胞进行基因改造来治疗镰状细胞病,从而改变了她的生活。
在这场激烈的伦理辩论中,有两大区别。一种是用于治疗的基因组修饰——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等严重疾病——和用于增强的基因组修饰。后者是像“停止设计婴儿”这样的组织所关注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因为它肯定会引起社会的担忧。但该领域很少有人认为它是可取的或可行的,因为人们可能想要增强的大多数特征——比如智力——都有一个复杂的遗传成分,涉及很多基因,基因编辑无法对这些基因进行有意义的改变。在治疗学中,大多数被靶向的疾病都是单基因的:只需要破坏或改变一个基因,这使得Crispr等工具更加有效。
允许任何人类基因组编辑显然不会为“设计婴儿”打开大门
另一个区别是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组编辑。在前一种情况下,以格雷的治疗为例,身体细胞发生的变化不会被后代遗传,因此不会对后代产生影响。当不存在有效的替代方案时,很难看出对体细胞基因组编辑减轻痛苦有什么反对意见——尽管目前非常昂贵的这些治疗方法的公平性和获得性仍然存在重要问题。种系编辑的争议要大得多——该领域的一些工作人员希望禁止它,许多人同意诺贝尔奖得主之一、Crispr机制的发现者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的观点,即在我们讨论伦理问题时,有必要暂停这种编辑。
因此,允许任何人类基因组编辑显然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为“设计婴儿”打开大门。但他们对过于仓促地接受高科技、引人注目的解决方案的警告当然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可能有其他的答案(比如通过对胚胎进行基因筛查来识别疾病突变)。他在2018年的噱头应该受到谴责,部分原因是它甚至没有针对原本没有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也没有效果)。
最直接的问题是这些编辑方法是否安全。即使有了Crispr,也有脱靶编辑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化学家David Liu在峰会上描述的使用Crispr-Cas9 dna剪切酶的更精确工具可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原因之一。虽然正常的Crispr以特定序列的方式切割DNA,但修复工作留下了很多机会。刘开发了一种叫做基础编辑和启动编辑使一种特定的DNA碱基能够精确地替换为另一种。1碱基编辑已被证明在体内有效地“纠正”镰状细胞2和Hutchinson-Gilford综合症3.(导致加速衰老)的小鼠突变。它现在正在进行镰状细胞病、地中海贫血、白血病和其他疾病的人体临床试验。人们普遍怀疑刘晓波最终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是的话,希望是在化学领域——因为这确实是最高阶的化学。
参考文献
1 A V Anzalone等,自然, 2019,576, 149 (doi:10.1038 / s41586 - 019 - 1711 - 4)
2g A纽比等,自然, 2021,595, 295 (doi:10.1038 / s41586 - 021 - 03609 - w)
3 L W Koblan等,自然, 2021,589, 608 (doi:10.1038 / s41586 - 020 - 03086 -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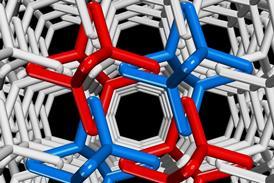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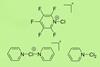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