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有影响力的科学外交家通过艺术教授化学,做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扎夫拉·勒曼(Zafra Lerman)是马耳他会议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将来自中东各地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促进该地区的合作和和平。除了在科学外交方面的工作外,她还因其通过艺术教授科学的创新方法赢得了许多国际奖项。
从两岁起我就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我会对着镜子问,‘我在那里做什么?“我不知道科学家这个词,但我知道我想知道更多关于科学家的事情。
我研究了次级同位素效应。我的一个关于二次同位素效应的温度依赖性的发现开始了其他人的研究。但是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想我可以教那些永远不会学习科学的少数民族,教非科学专业的学生,这样他们就能理解日报上出现的科学文章。
迈克·亚历山德罗夫对一所大学的愿景是开放招生,这样经济困难的人就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接管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学院时,那里没有任何科学,因为那里的人都很进步。他们说科学导致了所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教这么可怕的学科?但他想要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教师,参与裁军,军备控制和人权。我的名字到处都是,他给了我完全自由的手去做我想做的事,我想怎么做。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老师,因此我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教化学。我使用了美术、音乐、舞蹈、戏剧、诗歌、动画,任何东西。一组戏剧专业的学生表演了一出戏剧来展示他们关于化学键的知识。他们把《罗密欧与朱丽叶》换成了钠和氯。几年后,我去看一场真正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说了一些话,在我的脑海里听起来像是“我是钠”。我去了后台,还是那个学生。他对我说:“我忘记了很久以前学过的所有东西,但是元素周期表和离子键我一直记在脑子里,因为我表演过,而且我对它们理解得非常好。”
当(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制作关于环境的视频时,这很有趣[难以忽视的真相他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我的学生非常生气:‘看我们的视频比他的好!传达的是完全相同的主题!没人给我们奥斯卡奖。而且他们比他早了好几年。
我使用了美术、音乐、舞蹈、戏剧、诗歌、动画,任何东西
我晚上在舞蹈工作室教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一年戈登科学可视化会议的组织者问我,你能不能带20个这样的孩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是如何理解的。他们来了,他们用舞蹈展示了化学键,用舞蹈展示了臭氧层的消耗,观众们都站起来高喊‘太棒了,太棒了!“可悲的是,观众都是白人,这些孩子都是非裔美国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告诉孩子们,他们将与杰出的科学家一起度过五天,他们会待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互动。我忘了说的是戈登会议是在拥挤的宿舍举行的。在他们看来,他们要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当他们到达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这里有叛乱’。所以我过去问,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你说过我们会和科学家呆在一起。那些宿舍很脏。为什么我们不跟科学家在一起?’所以我对他们说,‘是的,科学家们将在你们旁边的房间里。他们都留在这里。 You can learn from that – the type of the hotel is not important to these scientists, to them it is more important what they do for the world.’ But the dormitories really were bad. It was 100°F at night and there was no air conditioning.
然后我对孩子们说,有一个房间里有软饮料和零食。去那里,你将能够与所有这些科学家互动,正如我向你们承诺的那样。于是他们就去了,后来我进来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因为每个孩子周围至少有三个科学家,为他们倒可乐。我说这真的很奇怪。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对孩子们说:“哦,我看到科学家们对你们很好。”他们说‘是的,当我们来的时候,他们看到20多岁的非裔美国青少年,他们说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说了密码,我们说了“Zafra”。我告诉科学家们,你们刚刚知道不能以肤色来判断一个人。
这对科学家和学生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孩子们无家可归,但他们中有很多人上了大学,还有两个继续读博士。这就是化学的作用!但这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教授的。
我说服我的委员会去做所有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曾担任美国化学学会科学自由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25年,从一开始直到被拆除。我说服我的委员会去做所有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迫使美国政府给了我们去古巴演讲的许可证,并设法为古巴人获得签证,参加2002年在佛罗里达举行的美国化学学会会议。
9月11日我告诉我的小组委员会,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集中精力解决中东问题。然后,在2002年的会议上,美国癌症学会说,我们想要从框框外获得一个伟大的想法。我建议我们组织一次会议,把中东各地的科学家都请来,他们会住在同一家酒店,一起吃饭,五天之内不会分开。我说过我会带六个诺贝尔奖得主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古巴人说他们以为房间里有炸弹。你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这太令人震惊了。但是ACS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们计划在2003年12月举行第一次马耳他会议。
在我的小组委员会里有斯坦利·兰格,他在RSC国际办公室工作。他立即表示:“我认为应该让RSC参与进来。”最终说服了RSC。然后我们联系了德国化学学会的执行董事,他们加入了,我们联系了IUPAC, IUPAC也加入了。教科文组织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赞助商和支持者。
我们在起义期间举行了第一次马耳他会议。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在中东获得尽可能多的和平与稳定,因为这将有助于解决巴以冲突。董事会问我,为什么是马耳他?我说过,到达那里非常复杂,恐怖分子不值得去那里。我必须承认,在第一次会议期间,我们有安全措施,但只有我和组织者知道这一点。
我的目的是通过一次会议来证明不可能的任务可以成为可能。我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人们哭着,拥抱着,亲吻着,看起来就像一个家庭团聚。参与者说,“我们想要继续,我们建立了合作,我们建立了友谊”。所以我们进行了投票,他们一致同意进行第二次投票。
12月,我们本该举行马耳他X,举行盛大的周年庆典。但马耳他对Covid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来自马耳他暗红色名单上国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进入。我们有五个国家是深红色的。马耳他只批准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的疫苗。拥有其他疫苗的国家不能入境。所以100人中有50人不能参加。我们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做出推迟的可怕决定。人们悲痛欲绝。但这不是一个可以虚拟召开的会议,也不是一个可以混合召开的会议。 The conference needs the interaction.
我丈夫和我总是有歌剧季票,去交响乐,去芭蕾,去剧院。现在,因为我丈夫去世了,我带着我的学生或以前的学生,因为我不喜欢独自去任何地方。
我还在从事人权方面的工作。教育仍在继续,为和平而努力。还在努力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星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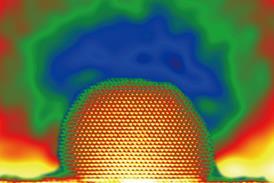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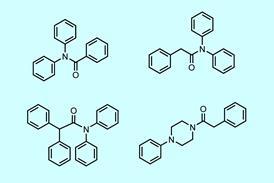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