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m,性别和性少数群体在工作场所的平等仍然是一个白日梦
Sofia Kirke Forslund早在大学时,她就知道出生时分配给她的性别不适合她,但她不太确定自己的确切性别身份是什么。弗斯隆德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她决定把探索放在一边。她说:“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可能理解我,我就会错过很多机会和合作,而且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把握,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
然而,压抑自己的性别认同给这位计算生物学家带来了情感上的伤害。弗斯隆德说:“每次社交都有点压力,因为我觉得人们看不到我的真实身份,不管我是谁。”“我觉得他们是在和一个不是我的面具互动,这让我很疲惫。”
幸运的是,福斯隆德在读博士后期间遇到了两位酷儿科学家,他们激励她做自己。她说:“从那时起,我开始逐渐尝试着测试我所能表达的界限,并努力确保我至少把自己的古怪表现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确信,如果我走得更远,我在职业上确实依赖的人不会感到惊讶,也不会攻击我。”
Forslund在2017年博士后结束时开始了她的医学转型,然后在2018年搬到柏林,开始担任柏林大学的首席研究员Max Delbrück分子医学中心在德国柏林。
在那里,她在加入之前向招聘人员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因为我意识到,如果我在接受新职位时不这么做,我就会一直担心:现在这么做安全吗?我还需要再等吗?”她说。
虽然Forslund最终在竞争激烈的科学界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但许多酷儿科学家却没有。即使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LGBTQ科学家的职业道路上也往往布满了异性恋和顺性科学家同事从未面临过的障碍。
没有归属感的感觉
一个科学的进步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来自21个专业协会超过25000名Stem专业人员发现LGBTQ+社区的个人比他们的非酷儿同事更有可能在组织中遭遇歧视和骚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称,同龄人的行为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到被社会排斥。此外,在过去的一年里,LGBTQ+专业人士睡眠困难的可能性比异性恋同行高出41%。
同样,2019年由物理研究所、皇家天文学会和皇家化学学会对LGBT+物理科学家和盟友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万博代理28%的LGBT+参与者曾考虑过辞去他们的工作-跨性别受访者的这一数字高达50%。
而Matheus de Castro Fonseca在巴西坎皮纳斯的巴西生物科学国家实验室(Brazilian Biosciences National Laboratory),这位细胞生物学家与更广泛的Stem社区的互动,尤其是在会议上,往往很尴尬。丰塞卡说:“(对我来说)提到我有丈夫是不自然的,就像异性恋者说(他们有)妻子或丈夫一样。”我们做自己感到不自在,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会作何反应。”
年轻酷儿研究者在教师层面上很少看到他们社区的代表,他们经常感到沮丧。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克里斯托弗·怀特海德他是瑞士巴塞尔大学的一名化学博士后,是一名同性恋,在他的领域找到同性恋导师尤其困难。“我在想,我能成为一名教授吗?我找不到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那我属于这里吗?他说。不过,后来怀特黑德在推特上找到了一些同性恋化学家的支持。同样,福斯隆德说:“我之所以总是如此害怕出柜,是因为我没有任何LGBT人群的榜样。”
学术界的系统性问题根深蒂固,往往阻碍了反对歧视和骚扰的善意制度政策。提到她所在公司的政策,Erika Merschrod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的化学教授、自认为是女同性恋的她说:“(他们)都写下来了,这就是支持。”我确实认为有一些你可以指出来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但说实话,除非有人做了可以直接被解雇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大多不受劳动法管辖,否则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有风险的,因为你还得和他们一起工作。”
支持性环境事宜
虽然不是每个酷儿科学家都觉得有必要在工作中出柜,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很重要——一个包容的环境可以让这个过程更容易。怀特海德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读研究生时决定出柜,因为他发现那里的工作环境很有利。他说:“教员们非常包容,非常开放。”
现在,怀特黑德发现不用躲在虚假身份后面是一种解脱。事实上,澳大利亚多元化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向同事出柜的员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创新与那些没有的人相比。怀特黑德说:“最大的好处是,它让我不会在试图注意自己说了什么或如何说话时失去精神和情感上的能量。”“我曾听人说,‘嗯,科学不在乎你爱谁。但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这方面;如果他们专注于隐藏自己的某些部分,或者试图对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很小心,这将使面试更难进行。”
LGBTQ+科学家也可能不会在不促进性别多样性的地方工作。露西Troman,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分校生物化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说,他们在选择工作场所的时候会考虑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我喜欢做我自己,也喜欢和其他酷儿打交道。因此,对我和其他想要表达自我的人来说,找到一个可以做自己的工作环境很重要。”“这比在一个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受到评判或不被重视的环境中要容易得多。”
原因之一是南希·威廉姆斯,她是WM凯克科学系的化学副教授,该系是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匹泽和斯克里普斯学院的一个综合系。几年前,她出柜是因为她想成为年轻科学家的榜样。威廉姆斯说:“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权威人士是同性恋,更不用说变性人了。”“直到2010年,我才认识变性人。所以,对我来说,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的,Eoin莫雷,德国马格德堡奥托·冯·格里克大学的一位同性恋神经科学家说,对他来说,做自己很重要,因为这可能会激励年轻一代。莫洛伊说:“我还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但看到有人能够做自己的工作,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可能会鼓励一些人,或者让一些人对进入科学领域感到更舒服,做自己。”
但另一方面,在外工作意味着酷儿科学家要承担更多的服务和指导任务。对威廉姆斯来说,这涉及到“坐在我办公室椅子上,只需要说话的学生”。这太棒了。这是我一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但我并没有因此升职。”
进行系统性的改变
当威廉姆斯几年前出柜时,她得到了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但她不得不在机构的系统中修改自己的名字和电子邮件。威廉姆斯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系统是以某种方式设计的,假设每个人都是顺性别。”他们认为没有人会改名字。或者如果他们改了名字,他们也会继续用原来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变革对多样性和包容性如此重要。唐纳德•郊游美国利哈伊大学负责公平和社区事务的副校长说,政策变化和教育的结合对实现这一目标非常重要。利哈伊大学的性取向和性别多样性骄傲中心在大学择名政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政策允许学生和教师轻松地改用与他们在大学系统中的法定姓名不同的名字。Outing说:“这有助于避免在交流中经常看到自己的死名字的创伤。”骄傲中心也在帮助推动大学更公平的家庭休假政策。
还需要更多关于LGBTQ+群体在科学中的代表性的数据。Fonseca说,这将有助于发现该群体在学术界的代表性不足程度以及原因。美国资助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告诉manbetx手机客户端3.0它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测试通过调查收集关于性和性别认同的数据的各种方法。美国化学学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性别信息中引入了“倾向于自我描述”选项在会员申请表内。
多样性和包容性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管理者在做出任何改变之前咨询酷儿员工是很重要的。有一次,丰塞卡拒绝参加一个专门为LGBT科学家提供研究成果的会议。“我想被并入集团;丰塞卡说:“我不想要一个特别的部分。”“我要谈的是我的科学,而不是我的性取向或性别。”
莫洛伊说,机构可以做很多简单的、经过考验的事情来表示支持。例如,在电子邮件中提到代词,而不管对方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它只是说:我知道其他人可能是不同的。他说:“我知道,对于那些在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方面略有不同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会很困难,而这种承认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息。”
同样,文化活动,如骄傲游行和庆祝LGBTQ+ Stem日(今年是11月18日)可以给酷儿科学家带来欢乐。特罗曼说:“如果你知道一所大学有骄傲月,即使你没有参加,你也知道他们是在鼓励、支持和接受你。”
LGBTQ+在科学和大学中的多样性
- 1
- 2
- 3.
- 4
 目前阅读
目前阅读
LGBTQ+科学家的日常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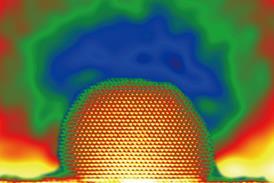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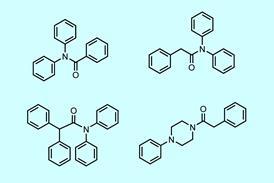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