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查普曼报道了那些因个人道德而离开祖国的化学家
“这一切都始于英国脱欧。在那之前一年,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我也拿到了奖学金。然后,那天早上,我们在新闻上看到了。它改变了我对英国的感觉,尤其是之后发生的事情。”In 2014, Christof Jäger had moved from the Cluster of Excellence Engineering Advanced Materials in Erlangen, Germany to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to start a new life with his family. Now, he’s leaving for Gothenburg, Sweden. ‘The prime minister [Theresa May] was saying that if you believe you’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you’re a citizen of nowhere. It gave us a bad feeling.’
Jäger的故事是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化学家所熟悉的。说到工作,我们通常会说为了职业晋升、更高的薪水或更好的生活质量而搬家。除此之外,离开一个国家通常是通过重大事件来考虑的,比如俄罗斯入侵后逃离乌克兰的学者。然而,对于许多化学家来说,尤其是那些拥有来自西方国家的特权并有资金搬迁的化学家,他们搬迁的动机更多是出于个人原因:归根结底是道德、政治以及他们的家庭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人才流失
近年来,由于政治转向右翼,这些决定有所加强,如英国的脱欧或美国的共和党。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化学家搬家回应案例是Alan Aspuru-Guzik,他是一位理论化学家,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离开了美国哈佛大学,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一次采访中自然Aspuru-Guzik称他的离开是“苦乐参半”,但考虑到政治的两极分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不在一个我不必担心下一个国家大戏的国家发挥我的技能呢?”他争辩道,“我可以专注于我的科学,和和我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
这并不总是等同于离开一个国家。在美国,不同的州可以根据谁控制州立法机构而对允许的研究有截然不同的法律,科学家的流动经常发生;例如,南达科他州禁止所有与干细胞相关的研究,而加利福尼亚州则以数百万美元的拨款支持这项研究。但决策过程往往不太关心什么是允许的,而只是生活在一个由共和党参议院管理的所谓“红色州”的经历(没有一个受访者提到搬离一个更自由或“蓝色”的地区)。
一位在礼来公司工作的化学家(要求匿名)从美国南部平原地区搬到了中西部,原因是他与邻居缺乏共同的价值观——从他们缺乏对生育权利和LGBTQ包容性的支持,到否认气候变化。现在,他准备再次行动。他说,这个国家似乎越来越两极化了。“也许只是人们在大喊大叫,但感觉空气中有什么东西。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之间都有分歧。这让我觉得我们正处于另一场内战的边缘。考虑到政治气候,这个国家似乎发生了一个我在道德上无法遵循的转变……他们称他们的敌人为“害虫”,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本打算为我和我的家人申请护照,但我们现在真的负担不起。但我一直在寻找可能接纳我们的地方。”
建立国际合作的困难很重要
Christof贼鸥
一些国家迅速利用了这种政治驱动的人才流失。当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法国总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发起了一项“让我们的星球再次伟大”的运动,让气候研究人员搬到法国。申请超过255份,而且最终是18位顶尖的气候科学家获得了法国数百万欧元的资助;其中13名科学家来自美国。英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2019年,科学与工程工会Prospect发现,其三分之二的欧盟成员正在考虑离开英国。而在2022年初,威康信托基金会的政策主管马丁·史密斯警告称,随着英国脱离欧盟,“聪明的年轻科学家将决定离开英国,这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是最好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英国有2020年净损失约1300名科学家美国的人才流失水平与巴西相当,仅次于印度。在英国退欧之前,英国一直是学术人才的净进口国。
外逃没有减弱的迹象。2022年6月,当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裁决,确立了堕胎的宪法权利时,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女王大学的化学家凯瑟琳·克鲁登(kathleen Crudden)在推特上表示,支持任何渴望移民的美国化学家。这个提议几乎立刻就被接受了。“两天前还有一个人联系过我!”克鲁登在7月中旬说。他说,去年有很多人非常认真、非常坚定地说,他们想搬到加拿大去。我不怪他们。我是说,我会的!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的很多学校招聘。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加拿大卓越研究讲座。对于招聘高级人才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目的是为加拿大引进新人才。
毫无疑问,这些财务考虑与道德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Jäger说:“两者都有。”文化是发起者,但资金环境如何发展,尤其是建立国际合作的困难很重要。我刚遇到一位在英国退欧后离开英国的同事,他说,由于英国的(政治不确定性),建立合作非常困难。现在,英国目前还没有科学部长,谁知道我们未来的资助机构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也在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家庭事务
然而,简单地说选择是关于伦理和政治的,不足以解释大多数希望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的科学家的决策过程。虽然道德可能是单身科学家唯一关心的问题,但那些有家庭的科学家通常会根据孩子的最大利益做出决定——通常会以相对较高的工资为代价。
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级化学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决定离开美国。“我们本来有机会留下来,”他解释说,“但我们决定不想让孩子在这样一个暴力的国家长大。不仅是枪支法,还有所有电影都美化暴力。”
我没有勇气把女儿们送到学校,整天担心再也见不到她们了
Rae劳伦斯
加拿大人雷·劳伦斯回忆起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完成学业后,她也做过类似的决定。“我在2000年12月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在乔治·布什当选之后。我看了看站台,立刻想到是时候回加拿大了!”Almost two decades later, when looking at her next career move and with positions not available in her home country, the politics of America once again affected her decision making. ‘I looked at America, and it was just during the Trump years. I felt politically disenfranchised … back when I was living in Missouri the Columbine shooting happened, and as children weren’t on my radar I never thought too much about it. But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school shootings over the years. Now I have two daughters, and our move would be around the time they’d start school. And I did not have the emotional strength to be able to drop them off at school and worry all day that I’d never see them again.’ Ultimately, Lawrence decided to work in the UK. ‘But if it had just been me, I’d probably b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lapping up the sun and living like a rockstar, because the salaries are so much higher!’
Jäger表示同意:“你是作为一个家庭做出决定的。”“我在德国长大,所以(离开英国后)回到德国会更容易一些。但很明显,瑞典对孩子们有好处。我们坐下来讨论:“这是我们想让孩子成长的地方吗?“相反,由于中东一些国家的人权记录,Jäger不被允许搬到这些国家。他说:“我有同事去过那里。”“作为一个有家庭的人,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我会感到不舒服。”
克鲁登说,这种对家庭生活的考虑是促使美国同事搬到加拿大的真正原因。“美国的整个基础是,无论你是谁,你都能成功。你不需要是什么领主的儿子。但在美国,随着财富不平等,它已经远离了这一点。现在,美国梦可以在加拿大实现了。”
尽管克鲁登意识到他们的动机,并支持他们的选择,但她仍然对事情发展到科学家们离开美国的地步感到难过。她说:“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坦率地说,作为它的(加拿大)妹妹,我确实希望他们能纠正错误。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拥有惊人的成就,如果这些成就减少或被侵蚀,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这种情绪再次表明,科学与政治无关的概念是一个谎言。最终,有才能的化学家会摆脱困境;而且,在政治观点两极分化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被剥夺公民权的移民不太可能很快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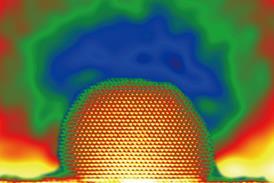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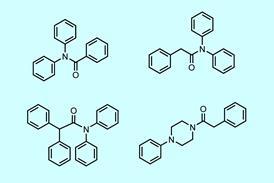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