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正确的支持,即使在封锁期间,研究事业和儿童保育也可以平衡
去年,尼达Rehmani她很兴奋能在纽约参加一个科学会议,这是她女儿出生后的第一次。她的丈夫也是一名科学家,以Rehmani的身份照顾他们17个月大的女儿,Rehmani拥有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智库工作Stem倡导协会在美国,他们从一个大厅跑到另一个大厅,参加不同的会议。当雷马尼努力集中注意力时,她的兴奋逐渐消退。她说:“我记得我听到大厅外不断传来(孩子尖叫的)假警报。”她想,这可能是孩子的咯咯笑或喃喃自语。但每次虚惊之后,她都会去看看女儿。
为人父母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一个2015皮尤研究中心一项针对美国父母的调查发现,超过40%的有孩子的女性和20%的有孩子的男性认为为人父母阻碍了他们的职业发展。然而,这个问题在科学家中似乎尤为严重。一个2019年的研究刊登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有43%的女性和23%的男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放弃了Stem工作,这一数字令人咋舌。
为人父母的成本

《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研究人员在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发表的论文数量会直线下降《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在2019年。这是事实艾玛巷她是英国卡迪夫大学药理学高级讲师,有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如果你有全职的学术生涯,你就有教学和行政职责,研究就被挤出了业余时间。一旦有了孩子,空闲时间就消失了,”莱恩解释道。初为父母的人可能也很难在工作中找回以前的活力。莱恩说:“可能一整晚都和孩子们在一起,知道你必须进来,进行合理的教学,并被驱使——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一些轶事证据——主要来自期刊编辑的推文——表明世界各地的Covid-19封锁可能对女性研究人员的投稿率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她们正在经历在线教学和在家教育自己孩子的新领域。美国华盛顿特区地震学联合研究机构的地质学家兼公共宣传官员温迪·博洪(Wendy Bohon)可以证明封锁带来的额外挑战。虽然她可以在家做大部分工作,但还要照顾5岁的双胞胎儿子和十几岁的继女,这让她更加困难。博汉说:“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父母,我觉得自己在工作上很失败,我的效率也很有限。”她的丈夫帮她做家务,但他的工作结构不灵活,这限制了他参与家务。
这并不是说只有女性的职业生涯会受到父母身份的影响。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化学与石油工程助理教授詹姆斯•麦克科恩(James McKone)说:“我能投入到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必然减少了,因为我选择花时间陪伴孩子。”“为了哄女儿睡觉,我现在几乎不熬夜了。”
为了花更多时间待在家里,许多科学家父母牺牲了旅行和社交机会。调查结果发表于JAMA肿瘤学2019年,超过一半的女性受访者(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表示,养育子女的责任使他们无法参加会议。
2018年,45名研究人员组成了“科学中的母亲工作组”,发表了一篇评论一块关于他们在前往会议途中所面临的困难.总体而言,为儿童保育费用和哺乳室提供财政支持是他们对会议组织者和工作场所的主要建议之一。父母们也可以从这种趋势中受益在线会议由于冠状病毒,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参加会谈。
找到你的村庄
在工作和家庭中获得支持可以帮助父母管理儿童保育和研究雄心。计算植物生物学家安娜Matuszyń斯卡尽管有两个孩子,但《纽约时报》的出版产出并未受到影响。matuszyzynska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她的合作伙伴的支持至关重要。她说:“最终你会回到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分担工作。”“没有哪所大学的支持项目能解决家里的问题。”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Chandrima回家,一个生态学家授予顾问威康基金会/DBT印度联盟,在忙碌中建立支持网络。在印度北部拉霍尔和斯皮提的一个村庄对家狗进行实地调查时,霍梅与村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她发现村民中有一个很敬业的人,在她女儿外出时照顾她。霍姆说:“他什么都学会了(比如换尿布),真的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我的女儿。”

洁Shanata,美国爱荷华州芒特弗农康奈尔学院的化学副教授说,选择一个符合你需求的校园很重要。沙纳塔和他的妻子是同一所大学的教员,他们选择了一个小镇,因为他们想避免长时间的通勤。这一决定也让他们六岁的女儿能够无缝地融入他们的工作生活。莎纳塔说,2月的一个周末,“我们每个人都有办公时间,我周六带女儿来上班,她周日带她来上班。”这意味着对方(那天)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在疫情封锁期间,沙纳塔和他的妻子一直分担着照顾孩子的责任。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沙纳塔的教学职责比妻子少,所以他自己承担起了为女儿提供实用科学课程的责任,帮她制作洗手液,并教她洗手液背后的化学原理。她发现与世隔绝特别难受,所以她也一直在给他妻子的所有学生写信。但沙纳塔说,在封锁期间做父母比正常情况下更具挑战性,“部分原因是我没有教一年级学生的专业知识、培训或背景。我教大学生。”
让别人听到你的话
有时候,你必须愿意在工作中要求某些权利和特权。当Bohon的双胞胎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经常需要每天抽几次奶来喂饱他们。哺乳室离她的办公室不是特别近,所以她不得不和大楼经理协商,为她提供一个小的私人空间来挤奶。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后的博洪说:“他并不是对它怀有敌意,他只是从来没有面对过它。”
产假对于减轻父母怀孕和产后的压力也很重要。matuszyzynska在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休了一年的产假,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休了八个月的产假——按照德国标准,她的工资是平均净工资的65%。但世界各地的产假法律各不相同——美国是如此没有强制性带薪假期尽管一些州和机构有自己的产假权利,这让许多父母不得不与雇主协商他们需要的假期。Bohon建议,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的科学家应该接触处于类似情况的人,以及倡导组织,如500名女科学家,她是该协会的成员。博洪说:“如果你被拒绝休产假……我们就可以开始向机构提出科学家个人无法提出的问题。”
Bohon还鼓励父母们从科学小组的工作母亲那里得到启示,在期刊上发表他们的要求。Bohon说:“科学社团是由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家对期刊文章、引用和基于证据的主张做出回应。”“所以当你有一个组织,收集证据,并以被他们的社区认可、理解和尊重的方式提出文章时,我认为它更有吸引力。”
找到平衡
并不是每个人在成家后都会回到全职的学术工作中。对Bohon来说,转向科学传播事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孩子的影响。博洪回忆说:“我没有很多人那样的流动性,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和一个伴侣。”“我想离我的家人和我丈夫的家人近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家庭的支持。它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更好的平衡,”她说。
材料科学家梅兰妮麦格雷戈,2013年,她暂时转向兼职工作,帮助她一边继续攻读博士后,一边抚养两个不到三岁的孩子。麦格雷戈现在是南澳大利亚大学未来产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说:“我做了不到一年的兼职工作,这有助于兼顾木乃伊和研究人员的责任,主要是减轻了人们在早退去看医生、去婴儿健身房等时候可能面临的一些内疚感。”
McKone说,科学家父母必须对幸福和成功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说,研究界倾向于根据数字来奖励专业人士——你发表的论文数量,你获得的资助数量,以及你指导的学生数量。麦克科恩说:“这对家长来说非常不利,因为没有孩子的教师几乎总是能够给出更大的数字,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他说,你必须在多少才算够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权威,因为更广泛的社区总是会告诉你更多。
幸运的是,他的雇主非常支持有家庭的科学家——他不仅获得了四周的带薪产假,大学还将他的任期评估期从5年延长到6年。
他说:“相比没有这个孩子、做更多研究的情况,少做些研究、有个我爱的孩子会让我更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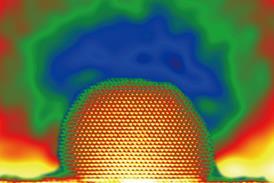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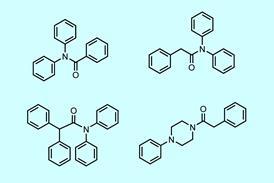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