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科学上很少有人走过的路

“你最初的故事是什么?”我经常发现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问完之后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在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到底被问了什么时,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默。
他们是在问我从哪里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答案很简单: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伦敦长大。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我既是格林纳达人,也是尼日利亚人,或者我想确定的非裔加勒比人。然而,我唯一可以在表格上打勾的选项是英国黑人(其他)。“他者”这个词让我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一旦我拒绝了一个词,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他者”是美丽的,一个自豪地坐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边缘身份的交汇处:黑人活动家、艺术家和化学家。这让我想起了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的话:“使我们分裂的不是我们的分歧。是我们没有能力认识、接受和庆祝这些差异。”
现在,25岁的我找到了自己的社区。一个舒适、有益、能让我蓬勃发展的空间。但如果你在10年前告诉我,我足够优秀,可以攻读博士学位,或者我可以成为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会像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那样,完全不相信地摇了摇头,然后走开。
那时候,尽管我有一个充满爱和自豪的加勒比黑人大家庭,我的自卑情结还是很严重。我很少觉得自己属于我上过的四所学校中的任何一所,甚至不属于这个国家。除了我母亲不知疲倦的职业道德给我提供的导师之外,我很少看到有色人种是教师、教育者或导师。然而,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缺乏多样性对我的自我观念和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神奇的治疗和家庭支持,我逐渐意识到伤害的程度,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自由的大学生活中成为一名自豪的黑人同性恋女性。
作为一名英国黑人,一个人的黑人身份一直受到质疑。我的黑是藏不住的,不像我的酷儿。我必须自豪地戴着它,尽管有人说它让我看起来很生气,或者让我的兄弟看起来像个罪犯。对白人同龄人来说,我太黑了,但对有色人种同龄人来说又不够黑,这种感觉导致了我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持续的孤立感和困惑。更不用说谈论种族问题时的沮丧了,我的哀叹得到的回应是“种族主义在英国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2020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黑人的斗争肯定还没有结束。
我从小到大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我有很多医学榜样:我的母亲是一名超声医生,我的父亲是一名护理人员,我的兄弟是一名医生。但科学世界对我来说仍然陌生——考虑到英国1.9万名教授中只有25名是黑人女性,这就不足为奇了。只有三个黑人教授在英国教化学。
其次,在学校课程中缺乏代表性。向我展示的科学家看起来像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而不是刘易斯·拉蒂默和爱丽丝·鲍尔。没有人告诉我们,世界上第一个内科医生是一个名叫印霍特普的埃及黑人,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黑人。我们不断剥夺我们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社会的世界广阔的科学史和其中的多样性。
认识到自己的特权并利用它来帮助他人是可能的
科学界必须变得更具包容性,并创建有利于每个人的支持和指导社区和网络。在英国,接受全面而均衡的教育仍然是一种特权机会。尽管如此,认识到自己的特权并利用它来帮助他人是可能的。我很幸运地在两位坚强的有色人种女性的指导下学习生物和化学。他们让我相信我可以在大学里学习化学;他们激励我去创作创造性的学费这是一项为来自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提供免费学费的服务。
学术界只有一个人,我的私人导师,激发了我超越自己能力的梦想。因此,我成立了学校的第一个化学学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成立了我的第一个组织——创意教学。虽然这很困难,但我已经成长为自己,并意识到我可以改变宇宙中我的角落。为增加包容性,非殖民化工作必须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现在,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导师、盟友和决策者来激励和支持他们进行科学研究。
额外的信息
想了解更多,请访问creativetuitioncollectiv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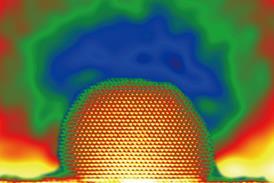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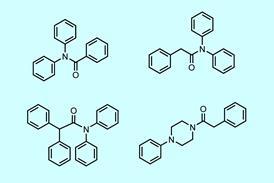








暂无评论